历史学话语体系构建须摒弃形形色色“中心论”
(本文来源:郭长刚等著《中国特色历史学话语体系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10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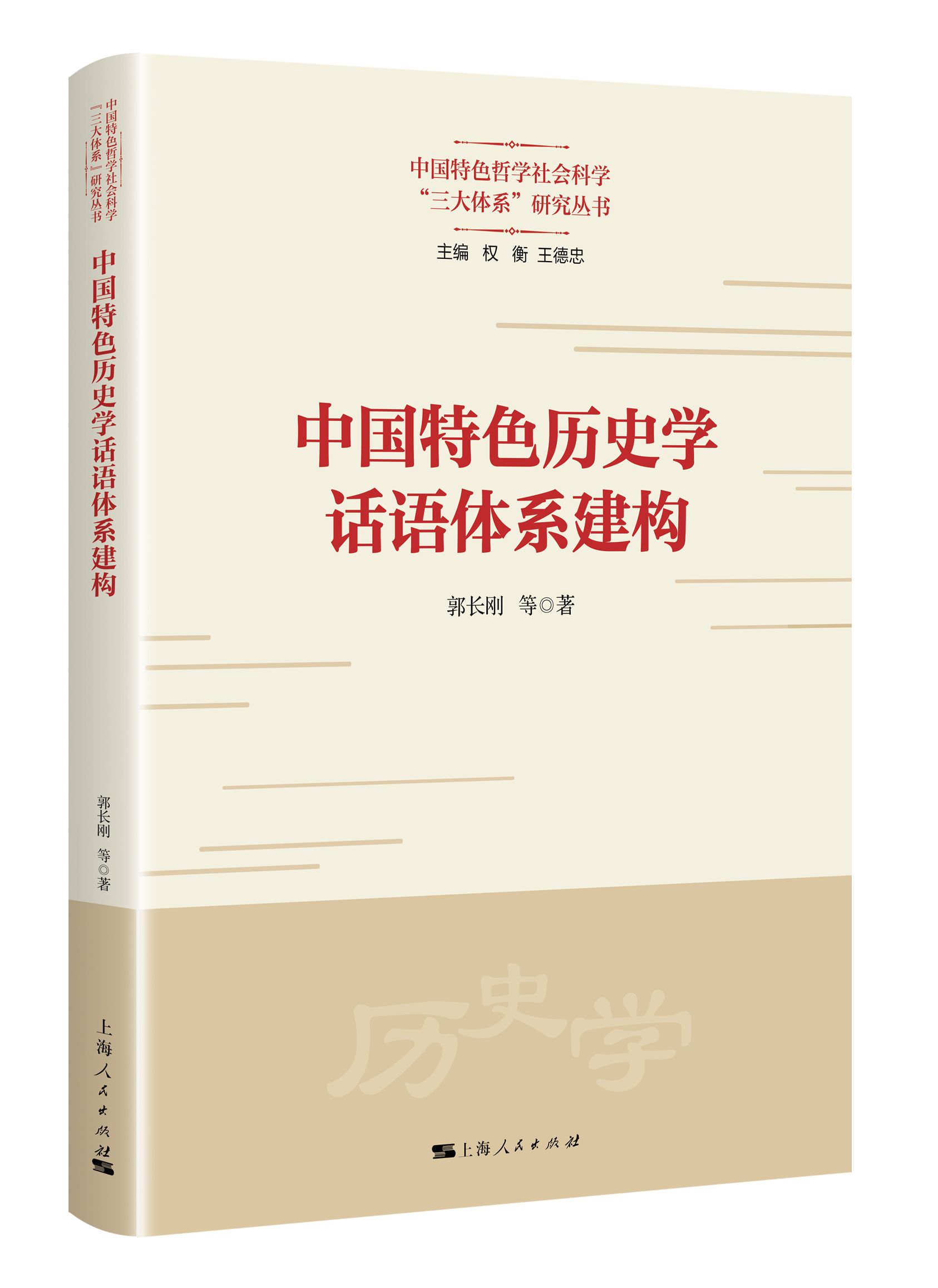
历史叙事既是对过去的认知和价值判断,也体现着对民族、社会、国家的认同感。近代以来,西方成为主导世界的力量,在西方的历史叙事话语体系中,西方社会成为“文明”“进步”“现代”的化身,其他社会和文明则被建构成为“他者”,成为“野蛮”“原始”“落后”的象征,整个亚洲被建构为政治上“东方专制主义”,社会发展方面则是“长期停滞不前”。在这一历史话语下,其他社会和文明就成了西方“白人的负担”,西方社会“统治”“殖民”非西方社会就成了符合自然规律因而也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是给非西方社会带去“文明”和“进步”,因而也就具有道德合法性。非西方社会要想“现代化”,就必须师从西方,走西方式的发展道路,总之一句话,“现代化就是西方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西方的殖民统治体系崩溃,西方中心论也随之被批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多极化进程正在稳步向前推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在逐步提高。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全球史的角度看,这个“新时代”其实并不仅仅是中国进入社会发展的新时代,更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新时代需要进行新的历史叙事,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或任何文明的经历只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1]这就要求我们在摒弃西方中心论的同时,也要避免陷入新的民族主义的或中心论的陷阱,要致力于构建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新的人类文明历史的话语体系。
一、百年大变局与西方模式的终结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是世界经济格局之变,也是国际权力格局之变,同时又是全球治理体系及治理规则之变、人类文明及交往模式之变。而所有这些“变”,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和去殖民化运动为前提的。如果没有二战后一百多个新的民族国家的独立,没有一个与旧有的以西方世界为主的资本主义体系相抗衡的新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的形成,这些“变”字将无从谈起。因此,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格局之变是不容忽视的。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个全球政治格局、经济秩序和社会文化历经动荡和剧变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一方面,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广大的第三世界是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寻求“去殖民化”,反对欧洲或者西方霸权。另一方面,同时代的欧美社会也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如民权运动、身份政治运动、反主流文化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反战运动等,尤其以1968年的学生抗议运动可作为其标志。需要强调的是,欧美社会的这些社会运动是“新左派”思潮推动下形成的,而这所谓的“新左派”,正是在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殖民主义运动的推动下才形成的,而且,在整个六十年代,第三世界的反殖民运动始终都在为欧美的社会运动、新左派知识分子提供着重要的斗争策略和理论资源。关于这一点,美国文化批评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曾经有过十分贴切的表述:“六十年代”有着一个“第三世界”的开端。[2]
随着二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广泛开展,西方殖民时代宣告结束,但他们的制度、理念等却作为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遗留了下来,许多新独立的国家几乎都按西方的制度模式组建起新的政权。如,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战线、印度的国大党、埃及的民族民主党等,都被西方自由、平等的世俗国家景象所吸引。整个西方世界也为此颇感自豪,认为“西方意识形态在第三世界的出现,不仅是西方政治影响力的胜利,同时也是西方送给世界公共生活领域的一份最好遗产”![3]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学院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还专门组织过培训班,学员主要是美国国务院的政策分析人士,他们的目标就是在结束培训后代表美国政府前往那些新独立的欠发达国家进行援助,指导他们如何按西方的模式进行政府机构的运转。[4]
但是,西方世界的这份“遗产”以及“援助”“指导”等,并没给那些新独立民族国家带来政治上的稳定和社会上的安宁。以埃及为例,1952年独立革命胜利之后,纳赛尔建立了一个西方化的新埃及,试图通过西方的政教分离观念以及西方式的政治制度来满足社会的愿望和需要,不遗余力打击传统的伊斯兰宗教力量。但在进入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代后,西方模式运转失灵,埃及社会对西方理念和制度出现“排异”现象,传统的宗教伊斯兰力量遂重新兴起,并成为政府体系的主要对手。萨达特为维持其政治统治的稳定,不得不拉拢穆斯林兄弟会,甚至还在自己名字上加上了“穆罕默德”字样,但他仍被指责为穆斯林的叛徒,于1981年被穆斯林兄弟会所刺杀。继任的穆巴拉克总统在努力维护西方模式政权的同时,致力于使自己的政权更具埃及社会的传统伊斯兰形象,但他最终也未能弥合埃及社会的分裂,不仅自己身陷政治悲剧,整个埃及社会也陷入所谓“阿拉伯之春”的大动荡之中。[5]
即使是“西化”非常成功的土耳其,自1960年代后期开始也在“西化”与“传统”之间重新寻找平衡。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后,阿塔图克·凯末尔完全按照西方社会的政治模式,推行严厉的世俗化的西方化道路。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土耳其国内出现左右两派的对立,又加上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得国内的各派力量的平衡出现了问题。在此背景下,传统伊斯兰力量复兴,纳杰梅丁·埃尔巴坎于1970年创建了第一个走向政治舞台的土耳其伊斯兰政党——民族秩序党。民族秩序党的领导者希望恢复传统的价值和制度,认为凯末尔主义者以西方模式取代伊斯兰以及奥斯曼国家的文化和传统是个历史错误,同时也是当代土耳其各种不幸的根源。他们的目标是要重建“民族秩序”,结束西方模式。[6]时至今日,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所致力于实现的“新土耳其”,其根本目标仍然是在国家政治模式上突破凯末尔主义,亦即突破“西方化”,强调伊斯兰传统和民主政治的结合,在身份认同上,更加强调自身文化的主体性,重视奥斯曼历史传统在维系和建构国民认同上的价值。
以上埃及和土耳其“西方模式”的发展困境,足可管窥西方的制度、模式、理念等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国家而言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更不是唯一正确的发展之路。其实,不仅是以埃及、土耳其、伊朗为代表的西亚北非国家,在广大的非洲、南亚、拉美等地区,西方模式也都引发了政治上的混乱和经济上的灾难。
因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正是从六十年代开始,广大的第三世界能够直接而“主动”地影响欧美社会的发展,致力于改变由西方社会主导世界秩序的局面,改变由西方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7]如果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间的那个时代可以被称为“轴心时代”,在那个时代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和思想都在同一时间内发生了决定性的历史性突破的话,[8]那么,二战之后以六十年代为肇始的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则可以被称之为“新轴心时代”,因为这是一个自由主义体系走向解体的时代:“一种在十九世纪还闻所未闻的与自由主义体系全然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兴起了。二十世纪初,自由民主秩序似乎正在顺利地发展,然而,共产主义制度——1939年以前仅限苏联——到1960年,已经扩大到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居住的地区。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在非洲,正在出现一种新型的政治组织”。[9]
同时,这也是“世界已经进入全球一体化的新阶段”,“现在世界上某个地区发生的事件不再可能象过去那样对其他地区不发生影响,二十世纪的历史名副其实是全世界的历史”。[10]在全球互动的形势下,致力于实现国家、民族、族群、性别等等各种身份的平等,反对造成各种不公的“强权”或“霸权”,在全球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社会运动人士的想象中,他们的斗争具有一个共同的终极目标,并形成一种“全球意识”,即对“主导性的权力结构、文化体系和日常生活的方式和行为发起挑战”。[11]这种挑战对欧美等西方国家而言,不仅事关他们所主导的外部世界秩序,也直接与他们内部的社会运动有关;对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对国际政治、国家之间权力结构发起的挑战,也就是反对殖民,追求民族独立。表现在理论上,就是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等理论的兴起,以及对现代性理论、西方中心论的摈弃;在历史学领域,则表现为由欧洲中心论向全球史的转向。
二、打而不破的西方中心论
二战之后,尤其是五、六十年代的去殖民化运动的迅速推进,让西方史学界认识到传统欧洲中心论世界观的局限性,认识到历史学著作的本质特征应该“在于它的全球性”,因此,扩展历史学家的视野“成为当务之急,并且成为当代历史学研究中的主要趋势之一”。[12]这一认识促生了“世界史”或“全球史”的书写。胸怀世界或全球的史家们试图超越民族国家叙事,如,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全球通史》中就声称,他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他所采取的立场,则“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是与站在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的。[13]
但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世界史”或“全球史”,其实主要是在物理空间上超越了欧洲或者西方中心,只是在内容上增加了“那些长期被忽视的地区的历史”,[14]如亚洲、非洲或者拉丁美洲的内容,但在历史演进的逻辑、历史价值观念的评判方面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固守着西方中心。如,1952年开始着手编纂,1963年开始陆续出版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六卷本《人类科学和文化发展史》(简称《人类史》),其欧洲中心论的倾向就受到各国学者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学者的尖锐批评。[15]苏联人编写的十卷本《世界通史》,也仍然以欧洲的历史进程作为世界历史演进的逻辑,其“世界历史概念甚至比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更带有西方中心论的性质”。[16]
国内学界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对欧洲中心论进行批判,新中国成立后到1960年代文革前,著名学者如雷海宗、周谷城、吴于瑾等都致力于打破欧洲中心论,编写中国特色的世界历史。雷海宗先生批判西方学界把世界历史等同于“西洋史”;周谷城先生通过对尼罗河流域文化区、西亚文化区、爱琴文化区、中国文化区、印度文化区、中美洲文化区6大古文化区的阐述,努力凸显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明的特征,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包括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吴于廑先生批判“欧洲中心论”把世界分成“文明的欧洲和落后的非欧洲”, 用欧洲的价值观念衡量世界。[17]但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西方中心论在我们的历史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并未被消除。在我们目前的史学话语体系中,西方中心论仍是一种普遍的(如果不是主流的话)存在。[18]
我们史学话语体系中的西方中心论集中体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学(世界历史)知识体系。在我们的历史学尤其是世界历史的知识体系方面,即在我们历史教科书以及历史著作里面,有关世界历史的书写都是围绕“西方”这个中心展开的。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书写仍然不足,如,除我们之外,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巴西、尼日利亚、孟加拉国、俄罗斯、墨西哥、日本、埃塞俄比亚、菲律宾与埃及是目前人口最多(超过一亿)的前13个国家,但除了美国、日本、俄罗斯3国在我们的世界历史知识体系中被较多关注外,其他10个国家都处于边缘或者被忽视状态。人口大国的状况尚且如此,遑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国家、广袤的中亚地区,以及遥远的有着33个国家和地区的拉丁美洲了。
其二,以西方历史进程作为标准参考体系的线性历史发展观。这主要体现在五种社会形态的由低级向高级的演进。根据这一观念,西方历史俨然成了“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被拿来强行裁剪我们的历史:中国历史上必须存在奴隶制,必须存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必须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等。其内含的逻辑就是:“将欧洲视作世界历史唯一的积极谋划者,某种程度上是‘源泉’。欧洲发布命令,其他地方服从。欧洲主动积极,其他地方被动接受。欧洲创造历史,其他地方在与欧洲接触之前没有历史”。[19]总之,“西方中心论”是把西方的历史发展进程当成了人类历史发展模式的“纯种”和“正统”,一切都以是否符合西方标准作为“历史合理性”的依据。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在历史的价值建构或目标意义评判上,西方被当成了“灯塔”,是“文明”“进步”“现代”的象征,其他社会和文明则是“野蛮”“落后”“原始”的代名词;整个亚洲被称为“亚细亚社会”,政治上是“东方专制主义”,经济上是公有制的自然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则是“长期停滞不前”,物质生产力方面至多是有技术,但无科学,没有产生科学革命等。西方被建构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发源地、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中心、历史进步的推动者,“只有欧洲人才能引领改革和现代化,其他地方的人不能”。[20]可以说,西方中心论之所以能够被非西方世界的我们所广泛接受,就是因为我们从根本上认可了西方是现代文明的缔造者和象征,是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引领者。关于这一点,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已敏锐地观察到了。他说,在1965年的第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当有一名代表认为1500年以后“欧洲的进化”是世界历史进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时,“反对这种观点的亚洲和非洲历史学家却寥若晨星”。[21]其实,这也是直到今天西方中心论为什么难以被摒弃的原因所在,因为它体现了西方中心论中“合理性”的一面。[22]
因此,我们要进行历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必须检讨和重新审视上述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学知识体系和话语叙事。
首先,要致力于解决有关“世界历史”知识生产的供给侧不足问题。在历史学尤其是世界历史的知识体系方面,以前受制于物质条件,受制于学者们的知识结构和语言能力,我们能够借鉴(说得直白一点是“照搬”)西方人的学术研究成果,采取“拿来主义”已经很难得了。但现在,随着我们综合国力的提升、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以及学术研究和交流能力的不断开拓,我们不仅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掌握了研究对象国的语言,也有充分的经济能力走出国门,开展学术交流、进行田野研究和社会观察。尤其是随着区域国别学被设置为一级学科,区域国别研究得以深入开展并逐步走向全覆盖,我们世界历史的知识生产能力一定会得到质的提升,编纂出突破传统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体现文明交流互动的全新的世界历史著作和教材完全是不成问题的。
其次,对人类历史的演进逻辑需要有新的阐释,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比历史的线性发展模式具有更强的阐释力。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根基于生产力的进步,根基于由生产力进步所带来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社会、国家或文明都要对促进生产力进步的技术进行“原创”,对应于某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权力运作方式也不一定一模一样。放眼历史长河,促进人类历史进步的重大“技术原创”往往首先出现于某一地点或某几个点,然后扩展开来,推动人类文明的普遍进步和繁荣。且不说人类源自非洲,导致文明产生的“农业革命”也是首先产生于某个或某几个地区,而推动人类社会进入轴心时代,然后在整个旧大陆形成前工业文明的铁器的发明和使用,也是首先出现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某个地区,但我们并没有因此建构所谓的“安纳托利亚中心论”“美索不达米亚中心论”“黄河中心论”或“赫梯中心论”等。
因此,西方在现代科学方面首先取得突破,也并不意味着西方就是优越的,甚至具有种族优势。现代文明也会像铁器文明一样,逐渐传播开来(事实也正是如此),最终形成人类社会整体进步的局面。最初出现农业革命的地区在铁器时代和工业时代并没有继续领先,曾经在农业革命和铁器时代相对落后的西方,却在工业革命时代超前了,但这也同样不意味着在下一个技术时代西方就一定继续领跑。如果以全球史的视野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每个文明、每个社会或国家的历史都是更广泛的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部分,都是通过文明的交流互鉴而发展进步的,在这个广泛的进程中,任何一方都不是“原创”了一切,也都不必然永远代表着“进步”。这就是历史演进和文明发展的真实逻辑。
第三,关于社会制度尤其是政体制度的差异问题。西方自诩为“民主政治”,视东方社会为“专制主义”,这至今仍然是西方中心论持有者的根本性理由之一。其实,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政治思想家们在探讨何为“优良政体”时,并不以政体形式为标准。他们认为,政体制度在形式上不外有三种类型,一是君主政体,或曰王政,即政治权力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一是贵族政体,即政治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一是共和政体或民主政体,即权力掌握在多数人手里。不管是何种政体形式,只要执政是为了整个国家和全体公民的利益,就都是好政体,无所谓优劣之分。但这三种政体也都存在着弱点,即容易退化腐败:如果把公权力私化,执政只追求个人或集团利益,那么这三种政体就会分别退化为暴君政治、寡头政治、暴民政治,都会变得糟糕透顶。[23]
不论是哪种政体形式,要确保其为善政,必须确保权力掌握在贤者、智者手里,因此,古希腊的政治思想家们特别重视执政者的知识和智慧,主张贤者、能者治国,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都认为“知识即德性”,主张贤人政治,主张专家治国,认为治理国家需要专业知识,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执政的,所以他们反对民粹主义,并不认同当时雅典的政体制度。总之,在古希腊思想家那里,判断政体优劣的不在于其采取何种形式,不在于是否票决,而在于其执政的目的,在于公权力为谁服务,即要执政为公,达成“社会正义”之善;同时,执政者必须具备治国理政的能力,一个好的政体制度必须体现政治智慧。概言之,“求善”和“求智”是古希腊政体制度理论的两大核心要素。
以文明冲突论为世人所知晓的美国学者亨廷顿,在1968年曾出版了一本著名的著作《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在该书中,亨廷顿开门见山指出“国家之间政治上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水平”。[24]他根据新兴国家的政治制度发展状况,论述了第三世界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遇到的种种问题,认为第三世界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必须有一个强大稳定的政府。他指出,二战后亚非拉一大批国家纷纷获得民族独立,都致力于现代化发展和建设,但到 20世纪 60年代,除少数国家以外,大多数国家不仅没有摆脱贫苦和落后,反而陷入了政治动荡和暴力冲突,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没能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因此,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转型中的国家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创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而不是像美国或西方那样追求“投票”“选举”的形式。[25]因此,当下西方社会的“自由民主”论,以及对东方世界的“专制主义”“威权主义”建构,更多是出于冷战以来的意识形态斗争战略之需。
三、不同视域下的西方历史话语叙事
历史学话语体系中的西方中心论是将西方置于历史进程的中心,置于民主、进步、文明的“高光”之下。其实,世界历史是一个从分散走向整体的互动交流的过程,从文明交流互动的叙事角度,对西方的历史可以形成完全不同的话语叙事。如,在社会发展模式及与其他文明、社会的关系方面,就会发现西方社会自古以来就把对外掠夺和战争作为解决自身社会发展问题的一种路径依赖,这已构成西方社会的一种本质性特征或曰发展“基因”。且不说更为遥远的古希腊人(西方)用于建构自我认同的特洛伊战争,以及公元前八至六世纪的大殖民运动,最迟至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人(西方)已经形成了通过对外战争和掠夺来解决自身社会问题的“集体意志”。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希腊城邦社会盛极而衰,各城邦间争斗不断,贫困成为社会冲突的根源。为了解决由贫困所造成的社会危机,维护希腊人的共同利益,哲学家伊索克拉底通过他的《泛希腊集会辞》祭出了“泛希腊主义”的旗号,呼吁“希腊人不应该攻打、统治希腊人”,希腊人应该通过掠夺东方波斯“野蛮人”的财富来解决内部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问题,认为征伐波斯的战争可解决希腊人的经济困难:“等我们摆脱了生活上的贫困,那时我们才能和睦相处,彼此间才能有真正的善意”。[26]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主义的观念,为亚历山大的东征波斯做了最有效的战争动员。
继希腊人之后的罗马人,把征服和统治其他民族视为自己的“天职”。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大诗人维吉尔的诗句给出了最准确的表达:“但是你,罗马人哟,记住,你要统治世界各族人民!这才是你的本分”。[27]
到了中世纪,1096-1291年近二百年间,罗马教廷动员整个欧洲的力量,对地中海东岸地区发动了10次掠夺性的十字军远征。十字军东征的原因有很多,但教皇乌尔班二世的战争动员却如同伊索克拉底再世。1095年夏教皇乌尔班二世前往法国做远征东方的宣传,根据修道僧罗伯特的记载,乌尔班二世呼吁说:“你们现在的土地,四周被丛山海洋包围,这狭小的土地无法容纳众多的人口,而且土地贫瘠,收获不足糊口。于是你们人吃人,进行战争,彼此杀伤。现在,但愿你们彼此间不再争吵仇视,而共同踏上去圣墓的征途,把那块‘流奶与蜜’的大地从邪恶民族手中夺过来,它就成为你们的产业……”[28]
在西方对外掠夺和战争的背后,是其自古就已存在,并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强化甚至是“理论化”“科学化”的种族主义逻辑。
古代希腊人把非希腊人称为“吧尔吧”人,即“蛮族”(barbaros,该词最早出现于《荷马史诗》第2 卷的《船表》),起初其实只是个拟声词,指操不同语言的人,所谓“异舌”或“异语之人”。但到了古典时代,经过大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等人的建构,最终演变为对一切非希腊人的蔑称。[29]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对非希腊人的“蛮族”进行了最为“经典”的理性论证,认为蛮族“天然都是奴隶”,因为世界上“有些人天赋有自由的本性,另一些人则自然地成为奴隶,对于后者,奴役既属有益,而且也是正当的”,因此,“野蛮人应该由希腊人为之治理”,希腊人奴役、统治蛮族非希腊人是天经地义的。[30]前文所说的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主义”,也是基于与亚里士多德关于“蛮族”观念的相同的逻辑,认为希腊人与蛮族人之间存在着对立,希腊人之间存在着共性和共同利益。伊索克拉底还认为:“让亚细亚人比欧罗巴人更强大,蛮族人比希腊人更昌盛,将是何等的耻辱!”“绝不能允许这类事发生,应该导致完全相反的局面”。[31]
古希腊人的“蛮族”观念为后来的罗马人全盘接受和继承。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就说过:“全体希腊人和外族人、野蛮人的战争是永恒的,因为决定他们是敌人的乃是天性,而非每日都在变化的因素”。[32]这应该是直至今日西方与非西方对立,西方存在着共性和共同利益的“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古代原型。
新大陆发现之后,西方殖民者不仅贩卖非洲黑人到美洲做奴隶,对美洲的原住民印第安人也大肆奴役、屠杀。在十六世纪中叶的西班牙还展开过如何看待印第安人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印第安人是否是有理智的生物,就是说,他们有无人的本性?”认为印第安人是低等的蛮族的一方以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所阐明的“蛮族”理论为依据,推论出印第安人属低等人种,“他们行为粗野,习俗丑陋,没有文化,只有最低的本能。因此他们断言否认印第安人具备理智,认为他们既然是低等人种就一定要从属于高等人种,要为高等人种效劳”。他们还认为“权威和财产是有理智的人的特征,而缺乏理智的人不应有任何权力,因此征占印第安人的土地将他们变成奴隶是合理合法的”。[33]
近代的欧洲不仅忠实地传承了古典时代亚里士多德、伊索克拉底的将非希腊人“他者化”的理论,更还运用近代科学革命的成果,把西方人(欧洲白人)与非西方人(有色人种)的对立“科学化”,建构出臭名昭著、贻害无穷的种族主义理论。
十八、十九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类的地位被彻底自然化,根据生物学的分类标准被置于动物系列中,原来《圣经》中所宣扬的人类同源论(同一祖先)被证明是假的。十八世纪的博物学家兼人类学家如林耐、布封、布鲁门巴哈、坎佩尔等对“人种”进行了分类。既然人可以被划分为不同“人种”,随着十九世纪进化论的兴起,不同的人种因“进化度”的不同而被赋予不同的价值,因而可以被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人种”的不同遂“被认为是性质不同”,不同人种之间存在着不平等也就自然而然了。[34]这便是近代西方殖民扩张、殖民奴役和殖民掠夺的逻辑原点。
美国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认为,种族的偏见可能和“已知的历史同样悠久”,生态社会主义者乔尔·科维尔也指出,“在历史上种族主义现象到处存在”“种族仇恨存在于人类的本性中”。[35]但是,把种族的偏见上升为“主义”,并以科学的逻辑论证某个人种对其他人种的占有、奴役、掠夺、屠杀等都是合理的,符合自然规律的,因而也是道德的,只有近代的西方才达到这一程度。惟其如此,法国学者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才指出,“种族主义是一种‘源于欧洲的现代现象’”,是一种“西方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实践”,它与一般的种族歧视思想不同,不能“与古已有之的种族偏见和种族压迫混为一谈”。[36]
二战结束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中心论观念、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观念等遭到摒弃和批判,以爱德华·赛义德等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把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东方主义等西方意识形态送上了审判台,近代以来以直接的殖民和掠夺为主要手段的西方现代化发展方式不能继续维持,但“掠夺”还继续存在,只是换成了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不再是之前的以枪炮武器等“硬实力”为表征的明火执仗,而是变科技为权力,变资源为权力,变经济、金融为权力,“把世界经济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以技术、资源、经济、金融的掌控为手段,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掠夺。[37]
如,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政界凭借其农业净出口达到全球的四分之三的优势,开始提出一项重要国策——对外运用“粮食权力”(Food Power),“将粮食出口管制作为外交谈判的重要筹码,并换取大量实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例如更强的中东事务干预、更优惠的石油购买价格、更多海外市场的准入机会等”。对此,时任美国农业部长厄尔·布茨就曾公开表示,“粮食是一种工具,它是美国外交谈判工具箱的一种武器”。[38]至于科技战、金融战、经济制裁等,更已经为世界所周知。
在财富掠夺的方式变得更为隐蔽的同时,掠夺的逻辑也变得隐蔽了,传统的以种族优劣论为特征的种族主义,转而为种族(或文化)“差别权”这种“不明言的种族主义”所取代。“这类种族主义既不靠近不平等,也不走向生物学上的种族。这类种族主义不援引纳粹的学说。这种种族主义既不出口伤人,也不明确呼唤仇恨”,但它强调自身的与众不同,鼓吹“文化之间差异的绝对化”。[39]当今西方社会以“民主、自由世界”“市场经济”自居,结成所谓“价值观联盟”,甚至搞什么“优先论”“例外论”,其背后的逻辑就是这种“新种族主义”,所谓“价值观联盟”也不过是近代史上“欧洲白人”的别称。他们宣扬民主和自由,其实并不是为了民主和自由本身,而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利益,正如有观察人士所指出的:美国在全世界宣扬、推行所谓的民主和人权,其实并“不是为了民主和人权本身,相反,他们是为了加强美国的安全,并进一步提高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民主和人权都是普世性的原则,但美国的政策并非如此,它们是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的。[40]
马克·布洛赫曾说过,历史学研究若要顺利开展,第一个必要前提就是提出问题,而历史学家工作的好坏,同提出问题的质量高低有直接关系。如何对待或者如何打破历史学话语体系中的西方中心论,就看我们“如何提出问题”,站在哪个立场上进行新的话语体系建构。破除西方中心论,“面临的挑战在于,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要让隐藏在区域历史之多彩地毯下的权力结构所起的作用隐而不见”。[41]因此,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叙事,不是要无视、否定、摈弃西方的文化创造、制度精神或技术发明,对西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等,也不是简单粗暴地放弃公元纪年、古代、中世纪、近现代等的断代划分,而代之以我们自己的某种纪年或分期法。关于这一点,正像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用印度或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的神话取代以欧洲为中心的‘殖民主义’的神话同样是劳而无功……‘我们必须抛弃中心和边缘的观念’,无论这个中心是位于欧洲还是位于中国”。[42]
人类历史是一个发展的长河,“你方唱罢我登场”是历史的“常态”(尽管我们期待着未来的“大合唱”)。作为历史学从业者,尤其应以历史的也就是发展、变化的眼光去审视不同文明间的姹紫嫣红之别,必须基于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认识,摆脱形形色色中心论的“丛林原则”或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窠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应该赋予人类(世界)历史发展以全新的内涵,我们的历史书写应该体现出时代的这一根本性变化。
本书的主题是中国特色历史学话语体系建构。历史学话语体系应该包括历史学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话语叙事体系等诸多方面,但要在一本书中全面涵盖历史学话语体系的各个方面是不可能的,故而本书主要围绕几个主题,在解构相关西方中心论话语的同时,致力于探讨中国特色的话语叙事。
本书第一章是关于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理论思考;第二章聚焦“东方专制主义”这个西方中心论话语的核心问题,尝试对其进行解构,并力图超越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叙事;第三章反思有关“民族国家”的西方话语叙事,阐释和合共生、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史观内涵,梳理中国传统的天下理念及与周边国家关系理念的世界历史意义;第四章审视西方现代化理论,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问题及重要发展路径,阐述中国特色海权观与海洋共同体理念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性的关系;第五章专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话语体系问题,尝试从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观察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的建构;第六章综述中国城市史研究中话语体系的范式迭代情况,思考城市史研究可能的理论突破,并以上海学、上海史、海派文化研究为切入点,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的视角,展示中国城市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与所面临的挑战。
以上内容框架,只是我们的一种尝试,期望能为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一种视角,贡献一份思考。
[1]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页。
[2] Fredric Jameson, "Periodizing the 60s." SOCIAL TEXT, no. 9/10 (1984): pp.178-209
[3] Mark Juergensmeyer, Global Rebellion: Religious Challenges to the Secular State, from Christian Militias to al Qaeda, p7.
[4] 约瑟夫·R·斯特雷耶:《现代国家的起源》,华佳、王夏、宗福常译,格致出版社2011年版,普林斯顿经典版序(二),第13页。
[5] 参见郭长刚:《全球地域化理论视域下的阿拉伯大动荡》,载《光明日报》2012年9月3日。
[6] 郭长刚:《土耳其“民族观念运动”与伊斯兰政党的发展》,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05期。另参见杨晨:《土耳其“民族观念运动”兴起的历史因由》,载《史林》2022年05期。
[7] 1960年代被认为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它孕育了多元政治格局和文化多元主义,宣告了一个传统的社会伦理和价值体系的旧时代的终结。众多研究者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雅德维加·穆尼等均认为1960年代是一个分水岭,关于1960年代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六十年代”或“全球六十年代”研究。
[8] 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他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把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一段时期称之为“轴心时代”,因为在那个时代,人类社会走出了传统的青铜时代,进入了“高科技”的铁器时代。铁器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财富的流动,于是造就出了一个新的富有阶层,这个新崛起的经济力量不甘心于政治上的无权地位,对当时由世袭贵族垄断社会政治权力的局面非常不满: “始于公元前750年前后的经济扩张,其主要结果是,经过一段时间产生了一个富人集团。这个集团……必然日益感到被排斥在政治特权之外,是非法的和不讲道理的”,他们要中终止这一社会状况。参见A·安德鲁斯:《希腊僭主》,钟嵩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4页。
[9]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页。
[10]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43、2页。
[11] Karen Dubinsky, New world coming: the sixties and the shaping of global consciousness. Toronto: Between the Lines, 2009. pp. 5-6.
[12]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1、148页。
[13]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
[14]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158页。
[15] 张广勇:《从文明中心的到全球文明的世界史》,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中译本导言,第43页。
[16]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48页。
[18] 参见顾銮斋:《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中的“西方中心论”问题》,载《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02期;仲伟民:《“西方中心论”的“非”与“是”》,载《学术前沿》2022年05期(上)
[19] S.康拉德:《全球史导论》,陈浩 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30页。
[20] S.康拉德:《全球史导论》,第130页。
[21]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53页。
[22] 参见仲伟民:《“西方中心论”的“非”与“是”》,载《学术前沿》2022年05期(上)。
[23]参见柏拉图:《理想国》第八卷,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以及波里比阿在其《罗马帝国的崛起》中对此也有述及,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四、五、六卷,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以及波里比阿:《罗马帝国的崛起》第六书,翁嘉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24]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25]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第8页。
[26] 何珵:《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集会辞>与泛希腊主义》,载《世界历史》2015年04期
[27] 特威兹穆尔:《奥古斯都》,王以铸译,译者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28] 杨真:《基督教史纲》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22页。
[29] 何珵:《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集会辞>与泛希腊主义》,载《世界历史》2015年04期
[30]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页。
[31] 黄洋:《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东方”想像》,载《历史研究》2006年01期
[32] Livy, Ab Urbe Condita, eds. B.O. Foster et al.,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XXI. 29. 15-16,转引自李永毅:《绝对知识的瓦解: 德里达与黑格尔》,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05期。
[33]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西印度毁灭述略》,孙家堃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页。
[34] 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高凌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9页。
[35] 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第2页。
[36] 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中译版序,第3页。
[37] 参见Manfred B. Steger, Globalisms: the Great Ideological Struggl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ird Editi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pp. 54-55.
[38] 参见冯维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人民论坛》2019年第32期。
[39] 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中译版序,第6页。
[40] Adam Wolfson, “Conservatives and Neoconservatives”, The Public Interest, Winter, 2004
[41] S.康拉德:《全球史导论》,陈浩 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30页。
[42]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1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