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晨评《奥斯曼帝国》|一部基于奥斯曼史料的帝国史
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 杨晨
2020-07-11 10:17 来源:澎湃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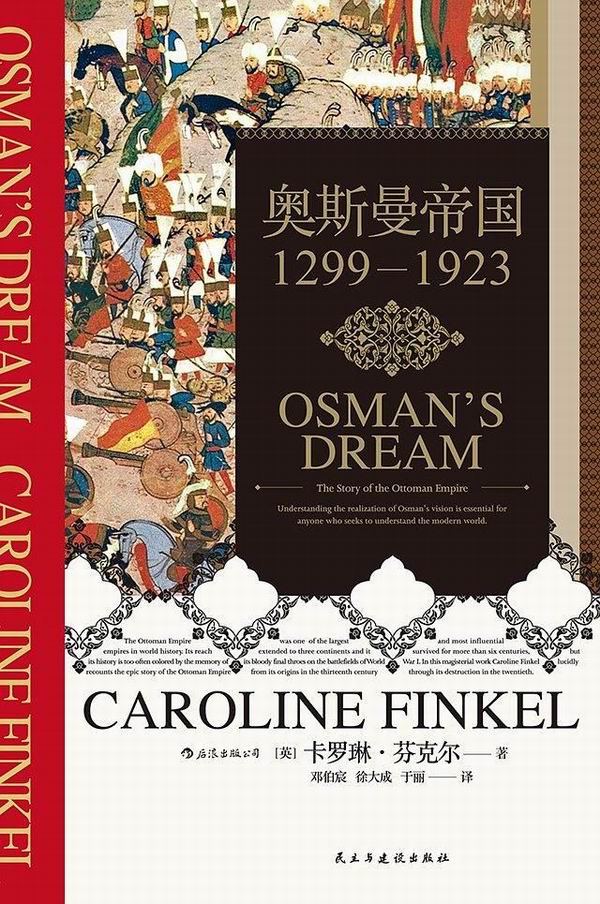
《奥斯曼帝国:1299-1923》,[英]卡罗琳·芬克尔著,邓伯宸、徐大成、于丽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150.00元
近两年,国内学界对于奥斯曼帝国的关注不断升温,相关的译著也开始增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帕特里克·贝尔福的《奥斯曼帝国六百年》(Ottoman Centurie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urkish Empire,2018),卡罗琳·芬克尔的《奥斯曼帝国:1299-1923》(Osman’s Dream:The 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2019),以及日本学人林佳世子的《奥斯曼帝国:五百年的和平》(2020年)。
这三本书的共同特点是属于通史性质,翻译流畅,可读性较强,但又各有各的特点。贝尔福在叙事中大量夹杂了个人的判断和评价,林佳世子胜在观点明确且独特,即奥斯曼帝国并非只是伊斯兰国家,而是“天下”,是拜占庭帝国,以及巴尔干、安纳托利亚和阿拉伯地区文化传统的继承者。而卡罗琳·芬克尔则以扎实的史料见长,使用了大量奥斯曼帝国的官方档案,意在挑战西方关于奥斯曼历史的“叙述传统”,呈现帝国及其人民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如何随着时间流逝改变对自己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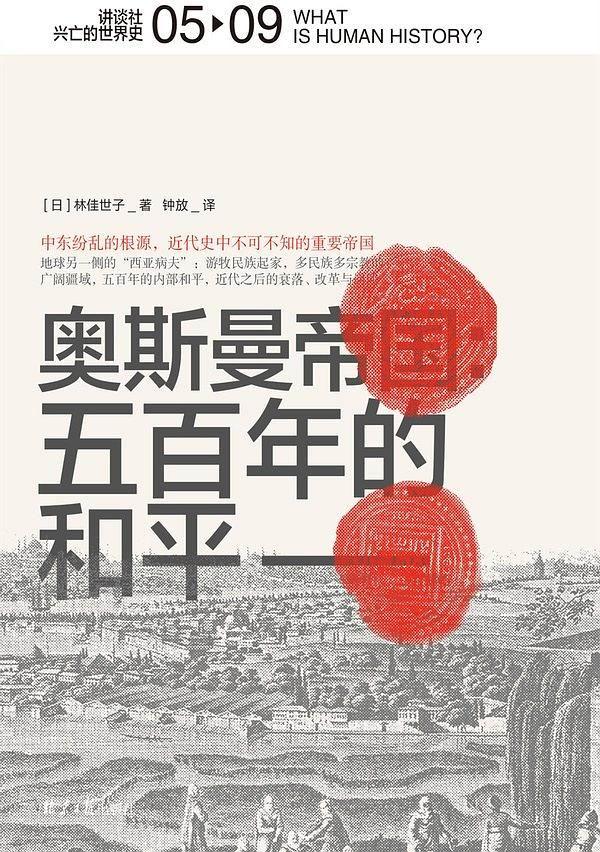
林佳世子著《奥斯曼帝国:五百年的和平》
一
奥斯曼帝国通史的撰写总要从帝国的起源谈起,但在这个问题上,恰恰由于缺乏史料记载而充斥着后世奥斯曼帝国编年史家的神话和传说。如十五世纪奥斯曼帝国流行的一种“奥斯曼梦”传说:第一位苏丹奥斯曼(Osman I)在梦中望见一轮明月自圣人胸中冉冉升起,迎面飞来沉入自己的胸中,然后大树自肚脐长出,树荫笼罩世界,树荫之下有山岭,小溪自各山山脚流出,有人取水而饮,有人莳花弄草,有人引水造喷泉,预示真主将皇帝宝座赐给奥斯曼及子孙后代。当然,此类传说距离奥斯曼的兴起已逾一百五十多年,可信度极低,但至少为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提供了合法性。
后世的历史学家在帝国起源问题上大致有两种看法。如韩志斌教授在《“加齐起源说”与奥斯曼早期国家的历史阐释》一文中所言,学界目前对奥斯曼帝国起源持两种看法,一种是“部落起源说”,认为奥斯曼帝国起源于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人部落,一种是“加齐起源说”,认为奥斯曼帝国是由“加齐团体”建立的,而“加齐”是一种边疆战士团体,主要从事攻击异教徒的“圣战”。
卡罗琳·芬克尔似乎中和了这两种看法,认为奥斯曼帝国的兴起是由于“掠夺联盟”的存在,这一联盟的成员里不仅有穆斯林战士,也有基督徒战士,而且土库曼战士只占少数,征战的快节奏使得更多基督徒自愿加入这一群体中,从而控制了拜占庭帝国和安纳托利亚的突厥帝国之间的边疆地带。边疆地带不仅吸引了大量了投机分子、无处可去只好随着边境变动变迁的人们,而且更重要的是托钵僧或穆斯林圣者也在其中,成为突厥-伊斯兰文化的传播者。
此外,在十四世纪早期,“加齐”一词并没有对抗性、反基督教的含义,虽然意思是“战士”或“攻击者”,但是除了指每位穆斯林皆有与异教徒战斗的天职之外,并不含有更多宗教训谕意味,因此早期奥斯曼穆斯林的宗教并无排他性,不仅穆斯林战士和拜占庭基督徒密切合作,通婚也是司空见惯之事,拜占庭杰出人士还频繁到奥斯曼宫廷任职。
无论是“部落起源说”“加齐起源说”还是“掠夺联盟说”,都部分解释了奥斯曼帝国的起源,但是奥斯曼公国并非第一波在安纳托利亚地区建立的穆斯林土库曼王朝。比如在十一世纪,达尼什曼德公国、萨尔图克人、门居切克人、阿尔图克人也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公国,这些土库曼人建立的王朝与西部的拜占庭帝国、东部的亚美尼亚人和十字军国家、南部的马穆鲁克王朝以及不断西进的蒙古帝国攻守变幻,交流频繁。
直至十四世纪初,安纳托利亚地区又诞生了新一批小公国,如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卡雷西、爱琴海附近的艾登、安塔利亚附近的帖克、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门泰谢、安纳托利亚中北部的桑达尔、内陆的哈米德、萨鲁汗、格尔米扬、杜尔卡迪尔公国等,还有奇里乞亚地区的卡拉曼公国以及与拜占庭领土相邻的奥斯曼公国,此时奥斯曼人才第一次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奥斯曼家族能够在强敌如林的诸公国中脱颖而出,短短两百年中就从一个小公国成长壮大为两大帝国的继承者,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是边疆民族不稳定的天性驱使奥斯曼公国不断开疆辟土?是不是因为奥斯曼公国地处拜占庭帝国防御薄弱的边境地带、在地理上具有战略优势,继而征服与之竞争的王朝?再或者奥斯曼公国的扩张是励精图治的苏丹、敏锐精准的政治谋略与福星高照的必然结果?抑或这些因素均是奥斯曼公国得以成为帝国的原因?这些问题仍然有待研究。
二
在传统的奥斯曼帝国历史叙事中,1453年至1566年是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时期,是帝国领土极大扩张、各种制度得以确立、中央集权得以夯实的重要阶段。
如林佳世子所言,奥斯曼帝国首先是一个巴尔干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后,穆罕默德二世立即展开了对半独立的塞尔维亚的征服工作,随后又于1456年攻打匈牙利人控制的南部重镇——贝尔格莱德,但惨遭失败。此后的二十年里,征服欲爆棚的苏丹,继续对巴尔干地区的罗马尼亚、达尔马提亚、阿尔巴尼亚(1468年),拜占庭在小亚细亚最的后一块土地特拉布宗(1461年),以及拜占庭在伯罗奔尼撒的海外领地摩里亚(1460年)展开征服行动,甚至还远征克里米亚半岛的意大利殖民地(1473年)和东方的白羊王朝(1475年),不过始终避免与强大的欧洲之盾匈牙利人兵戎相见。直至1522年,苏莱曼大帝才最终征服了贝尔格莱德。于是,在巴尔干的扩张被延缓七十年后,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对手变为哈布斯堡王朝。
奥斯曼帝国这一系列的军事征服仰赖于帝国中央集权的夯实和各种制度的确立。奥斯曼社会由统治者(Askeri)和被统治者(Reaya)两部分组成,即“军人阶层”和“民众阶层”。统治者包括苏丹、皇室成员、乌莱玛宗教人士、军事贵族等。军队由禁卫军(Janissary)、地方骑兵(Sipahi)和非常备轻型骑兵(Akıncı)组成。
禁卫军又称新军或耶尼切里军(Yeni Çeri),是十四世纪苏丹建立的一支对自己及王朝效忠的专职受薪军队,军人大多来自于战俘和奴隶,但奥斯曼人创造性地做了改进,实行少年征召制度(devşirme system),又译“德夫希梅尔”制度,实质上是一种“血贡”,将基督教男孩改信伊斯兰教并变成奥斯曼苏丹的仆人。虽然这种征召看似是残忍的,不文明的,但对于这些男童也并不是没有回报的,他们可以远离偏远、贫穷和受压迫的环境,有机会成为奥斯曼帝国王牌军的军人,甚至有权势的帝国官僚,而且并不会完全放弃以往的权利,部分人仍然与自己的家庭有所联系,成为奥斯曼帝国与巴尔干诸行省之间的联系纽带,但更为重要的是让苏丹获得了抑制其他当权的贝伊和贵族的实力。
地方骑兵也就是西帕希骑兵,一般也称为蒂玛尔(Timar)骑兵,他们被授权征收农民税,每个人都受封一块精确划定的土地或封地(蒂玛尔),受封的条件是他们有责任在战争时率领自己的人马参战。奥斯曼帝国的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都和这种蒂玛尔制度(Timar System)密切相关,苏丹将封地授予骑兵,这就解决了维持一支庞大军队而无须支付巨额现金的问题,而且这些蒂玛尔持有者不仅在战争时履行军事义务,还能在地方一级行政管理中发挥作用。不过,与当时欧洲的封建制不同,在蒂玛尔制度下,西帕希军人的土地不可以世袭,理论上说只是借用国家的,仅供生前使用,因此使得他们很难与地方社群建立密切关系,其拥有的军事权力也很难转变为实际的政治权力。
此外,奥斯曼帝国的继承制度既不同于蒙古和突厥人的“多子继承制”,也不同于欧洲的“长子继承制”,而是一种特殊的“独子继承制”,即王位继承权并不指定继承者,理论上所有的儿子都有资格,也都有能力获得继承王位的权利。一旦其中一位获得王位,那么其他兄弟都会被杀害,以保证苏丹之位的继承和平进行。为了确保继任的苏丹可堪大任,这些年轻的王子一般都被分配到各省担任总督,而最为中意的接班人被指派到离伊斯坦布尔较近的省份,其他的王子则远离伊斯坦布尔,以减少挑战执政苏丹的机会。这些王子们在各省担任王子总督时,他们的母亲在为儿子铺路。不过,奥斯曼的生育政治规定每位妃嫔只准生一个儿子,而且妃嫔多来自奴隶,因此这种“一母一子”政策的逻辑是避免外部势力插手皇宫内部事务。
少年征召制度、蒂玛尔制度和独子继承制等一系列制度的实施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奥斯曼帝国选择明君上位的概率,而且让苏丹手握一支强大的、没有二心的军队,强化了中央集权,以至于苏莱曼大帝在执政后期将自己比作“世上所有王国的所有者,所有民族面前真主的影子,所有阿拉伯人与波斯人中的万王之王,苏丹律法的发布者,第十位奥斯曼苏丹,成为苏丹的苏丹之子”,而与之同时代的欧洲统治者则有查理五世、弗朗索瓦一世、亨利八世和伊凡四世,可见苏莱曼大帝的豪迈气势。
三
按照西方学术界的看法,苏莱曼大帝为奥斯曼帝国戴上了极盛的荣冠,但他的去世也意味着帝国衰落的开始,直至奥斯曼帝国于1923年解体。这种观点也被称为“帝国衰落论”(Ottoman Empire Decline Thesis),曾经长期主导学界对奥斯曼帝国的研究范式。
这种范式的来源之一是当时奥斯曼帝国的知识分子,例如穆斯塔法·阿里,认为苏莱曼大帝之前的奥斯曼帝国虽然与萨法维、莫卧儿、乌兹别克等帝国相比缺少基于祖先的合法性,却通过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建立了符合普世正义的帝国秩序,但是从塞利姆二世时期起,甚至从苏莱曼允许宠臣干涉帝国事务起,这种切实的秩序就被破坏了。
在奥斯曼帝国知识分子的想象中,这种有序的世界是存在过的,苏莱曼就曾成功地使人们相信奥斯曼拥有一个公正的政体,但这种幻觉给奥斯曼政府带来了重重困难。奥斯曼帝国的政治与行政体制建立在帝国不断扩张的意识形态之上,但是随着十六世纪扩张速度的减慢,帝国开始无法适应出现的各种困难。得以开疆辟土的胜利越来越不容易获得,苏丹不再积极参与政府事务,不再御驾亲征,而王子们虽然不再因为继承权而惨遭杀害,却不再学习带兵打仗,只能被限制在托普卡帕宫的后宫之内,后宫干政、禁卫军反叛、大维齐尔当权变成了普遍现象。
这种范式的另外一个来源是欧洲人的记载。1571年的勒班陀海战和1683年在维也纳的围攻失败在西方的认知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认为它拯救了基督教世界,使其免受“异教土耳其人”的侵略。1683至1699年之间,为防卫远离埃迪尔内与伊斯坦布尔的边疆,奥斯曼的国力消耗已经达到极限,随后签订的《卡尔洛维茨条约》(Treaty of Karlowitz)成为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转折点。这一条约使奥斯曼损失了许多新近才获得的欧洲领土,而且领土丧失的方式也预示着奥斯曼的外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必须接受三十年战争后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制约,从此后欧洲国家意识到奥斯曼帝国的威胁已经不复从前,帝国开始走向衰落。
概括而言,关于奥斯曼帝国衰弱的原因有如下几点:脆弱的中央政府;权力不断增加的地方政府及其统治者;无法有效地获得税收;与西欧军事和技术上的差距越来越大;禁卫军的权力越来越大,但军事技术无法与西方相抗衡,不能继续推进军事征服;欧洲绕过奥斯曼帝国直接通过海路与亚洲建立贸易关系,帝国以往靠过境贸易获得的税收和利益就此失去;奥斯曼帝国的手工业者遇到欧洲制造商品的强烈竞争;欧洲大国和奥斯曼帝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允许欧洲免除关税;随着战争的不断失败,奥斯曼帝国不断赔款,越来越依赖欧洲的贷款,让欧洲人渗透帝国的经济,控制了税收等等。就如伯纳德·刘易斯所说,“奥斯曼帝国退变成了一个拥有中世纪心态、中世纪经济的中世纪国家,但却无力承担任何一个中世纪国家都无法承受的官僚和军队负担”。
不过,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奥斯曼帝国研究专家开始批判这种“帝国衰弱论”,主要出发点是基于以下四点。第一,奥斯曼帝国并非如西方所言是静止的、倒退的、没有任何创新能力的,而是一个不断流动和变迁的社会,自身的适应性极强。第二,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经济和思想进程比西方更早地展现出现代性的要素,奥斯曼帝国的现代性并不是西方影响的反应结果。第三,奥斯曼帝国和同时代的欧洲相比并不是独特的存在,不仅仅按照自己的规则和逻辑行事,实际上和欧洲国家同时存在于一个更大的世界网络之中,互相交往,互相影响。第四,“帝国衰弱论”忽视了奥斯曼帝国地方势力为挽救帝国所做的努力和尝试。也就是说,如果将一个拥有六百年历史的帝国简单地看成是前三百年“帝国强、欧洲弱”、后三百年“欧洲强、帝国弱”的二元对立,将帝国的历史用“一部兴衰史”来简单地概括,那么奥斯曼帝国的内部结构与变化趋势、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互动、交往、影响、互鉴等则将无处得知。
卡罗琳·芬克尔专长于奥斯曼帝国十六、十七世纪史,奥斯曼帝国军事史,曾有著作《战争的管理:奥斯曼在匈牙利的军事行动1593-1606》和《奥斯曼及其周边地区的地震1500-1800》。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她的这本著作《奥斯曼帝国1299-1923》偏重于利用奥斯曼帝国史料记载各种战争的经过及结果,对于帝国的制度、社会、文化等内容的书写较少,但即便如此仍然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立场也较为中立,对奥斯曼帝国研究的一些定论也有所冲击。另外,这本书并不容易阅读,是大部头,人名地名众多,这对于奥斯曼帝国研究者来说可能不存在很大的问题,但如果都相应地标注英文原文,或许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阅读体验将更加舒适。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089976
